叶圣陶杯佳作:有人睡了,还有一些人醒着?
点击领取>>>叶圣陶杯初赛决赛真题、高清录播课/大赛获奖范文集锦+写作素材+写作技巧
编者按:
这是一篇情景交融的散文,获得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初赛一等奖。文章从“烂柯”写起,笔触所及,有“烂柯”周边的山、水、人、物、景,作者对此不是客观的描述,而是作者的眼中的之景,心中之景,正所谓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冷静的深思与叙述中,表达出时代的更迭、文明的失落与繁华,作者用深厚的文字功底、散文的语句,在“烂柯”的神话中勘探现实的足迹。


烂 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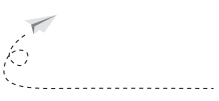
□姜熠晗 (浙江嘉善高级中学高一年级2班)
我醒了,她去了,白昼带来了夜晚。——弥尔顿
信安郡石室山,晋时王质伐木至,见童子数人棋而歌,质因听之。童子以一物与质,如枣核,质含之而不觉饥。俄顷,童子谓曰:“何不去?”质起视,斧柯尽烂。既归,无复时人。——南朝 梁·任昉《述异记》
作为一个家乡在烂柯足旁的人,我生活在神话的边缘。
说是故事也可以,我们村中并没有知道这神话的人,缺乏苍老声音在灯下的叙述,神话便只是一种特立独行。烂柯毕竟还在,它也还不是诺亚方舟,这是东方的道理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”也是西方的道理:“大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。”但神话的世界不仅仅是烂柯,如果它被埋没于遗忘之中,与消灭在天灾中其实并无差别。文化是为人而活的,而在如此巨变的时代,往日嗫嚅地瑟缩在神话中的文化,都在面临着永远失传的威胁。
其实失传是早就开始了,这是一个失传的时代。
从我无意识时弛缓的土路——“这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便也成了路”——与起伏尖锐的碎砖瓦路上碾来了现代主义的凯歌。那满载着水泥、玻璃、塑料、硅胶、披头士、丁克族、内卷……的列车正一秒钟一秒钟地将大地上的房子填埋起来。而我,我,一个自认为来自大山的小孩儿,正短暂地将脑袋从五颜六色的襁褓中探出,稳坐在列车的腹中,离开五颜六色的城市。车厢里不时嘈杂,不久大家便摊开在原始的大地上——这是汽车与列车的不同,汽车属于城市,而列车属于大地。相较于杰克·凯鲁亚克的轰轰烈烈的汽车,列车那一长串在暮色与四野间。分割而过的样子,总像是一种诞生,刚刚从母腹爬出来。
下车时同行的人屈指可数。旅行箱或背包颤颤巍巍地停在检票口前。穿着黑制服的检票人于是把玻璃茶杯在小桌上放定,站起来,捋平胸腹间的衣褶,茶叶慢慢往杯里沉下去。他接过你递上的车票,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抚你两下。有人用衢州话和他闲谈两句,他仍绞着舌头,坚持说普通话。日影探着猫须,指着小铁门外盘桓的人。他们是开大巴的,或开士的。以前,奶奶带我回时叫了一辆三轮车,蹬车的是个老头,弓腰急喘,一小时才到。不住地揉眼睛——汗滴进去了——他只要五块。奶奶和他说了什么,给他十元,他不要。失传了,现在三轮车也不见了。古城门镂出一个小圆形的夕照。我又看见那车夫有节奏地蹬着踏板。其实衢州的古城门一直都在,但我根本没注意,是他的背影才使我觉悟到这黑魆魆的存在。
这也就是烂柯的风度,烂柯的味道。尽管衢州并不缺山,但这沁在每个衢州人的骨髓里的温与慢的仪式,是专属于烂柯的因子。
烂柯周边,一路上都是灰蒙蒙的。无关乎衢州石灰石重工大城的身份,而是一切都在浅淡的色彩中休憩。灰是美的温床。只有停滞于灰的存在与准备成为灰的存在。灰是中正平和,是一无所有的白与无所不包的黑砸在怀里的灰。这灰来自鸿蒙,来自《千字文》里的“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”的世界。这灰是泥与焰,是江河的谰语,它落在大地上那就是泥土;落在田地上那就是面粉;落在牛河梁、龙山,那就是陶……灰非雾,但如雾苍茫,雾久化水,雾散去,灰在着。他起自泥,又回归泥,是大地的颜色。隔离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壁障之外,你感到它的存在,但到手、入目的永不是灰质,而是泥土、面粉、陶、灯末、车辙、浅笑、残阳……
在烂柯,生命或非生命渴望出色。万物一方面灰蒙蒙地混沌着,一方面又渴望着从不假思索中挣脱,就像一片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。于是我又看到那种被称之为“大山”的东西,嶙峋闪着幽暗的光,撕掉破烂的棉絮似的流云,一磊一磊地从天地的尽头吹着口哨涌过来。无。一切都凋谢的无。耷拉在这足旁的是乡村的躯壳,它是荒芜中唯一的繁华,身后跟着垂眉的大山。一滴灯火,四方如幕。我们依然被原始的力量所包围,从未突围过。千年的文明,掩耳盗铃而已。大山仍包围我们,睨着我们。封建、资本、社会、主义、主义、主义,人们都说世界变天,到头来只是一群狗牙齿勉强在大象身上抠出的一点儿零碎。夜郎自大。斜睨,这就是烂柯的表情。一切精致的利己主义、小资式的感伤、改天换地的击砭之心、沉鱼落雁、愤世嫉俗、淡然如水……在这里都要黯然失色,被斜睨着,像斧柄一样萎缩腐烂。在烂柯面前人无法出色,这是失传的真相。
一路走着,就有水声,是衢江的上游段。从烂柯的瞳孔里绵延而下,漫长而懒散,令人生畏。我蹲下去摸了一把,衢江就不是一个象征了,一股温而湿的气直透手心。远处江心上水波渲染了乌光——那是浮石,曾经的神迹,如今的区划名称。它如同座头鲸的脊背,温和而忠实地紧贴着我。听闻饮干江水的浮石会从那边传来它的鲸歌,但我却无以倾听。
江水过去了,烂柯安静地露出来。烂柯只有两块,洞天石梁以及包围着它的一切。包围者古朴静穆,毫无杂质,大山的杰作。被包围者,一塔一杯一巨棋,人的杰作。
石梁的边缘,塔的中心。它敦实地趴着地,敬畏天高云淡。沿窄梯攀援,黑暗的上升,仿佛让人模拟着回到母亲的子宫。透过小窗眺望,角檐被风洞开的孔罅更旷远于无极的四野。塔是古代建筑师手中针线玄奥的榫接,如同定海神针般半步不让,在历史的沙床上下去万仞。塔基以下是大地的肌骨,塔基而上,是人文的妙笔。塔的外部就是笔,在青灰的天空上划拉,而其内部如有五脏六腑。确乎如是,塔内常藏经书、舍利等等珍贵之物,包括塔自身的阴影。许多时候,塔是作为无味的山的视点而存在。它是烂柯的页眉。我仍然能记起,多年前的某个下午,在塔底旁采摘的蒲公英。彼时无知的我利落地把它压在字典里,以图得到什么标本。然而蒲公英虚无主义者的头部难以留存,只会在消亡前顺便弄脏几个词条。而无论是塔立足于隐喻的蒲公英之上,或是蒲公英自塔的缝隙里寻找遗忘与失传的土壤,在求剑的舟楫上,塔都留下一道清晰有力的刻痕。
碑,迷惘的东西。背着路标的外貌做浪漫主义的工作。线条与意境的狂欢。某种精致与自如合为一体的状态在笔墨间微明。隶、篆、草、楷、行甚至涂鸦分布其间。这组线条是怀素的云烟醉舞,那组线条泛着隶意、玄秘塔的骨骼;这组线条有永和九年的陈迹,那组线条有谁谁的迷狂。都是飘忽地绽放着,颇乏然而热烈的。我相见恨晚。其实杯本质上是种灰头土脸的东西,一坨岩石罢了。混沌欲开,似乎什么野兽正从梦里挣脱,黑雾要从碑的镇压下进入世界成个形,成为这世上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东西,像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什么的。石头是不动的,却感觉有巨大的力量在里面使劲,一旦挣脱了界限——生与死的,白天与黑夜的,无色与斑斓的,兴许什么都可以——也不过就是蚁啊牛啊丁香花啊诗人啊什么的。可惜,或是幸好,它挣不脱,只是永远在某种边缘上,欲明还暗的样子,很痛苦似的,但比真痛苦强烈多了。死去的,还要继续死。天地之间的那种生殖育化着的大痛大苦,说是很安详也可以。
在岩石上站定,直面洞天的是一张棋盘,懒散而处变不惊。大地上的一块空间将它的忧喜以一个坐标的姿态交付给弈者。棋才是一流啊,它只有黑白两色,却超越了一切对色彩的极致的赞美。蹙额执子,如同佛陀拈花的一笑,是一,也是万千的微妙。每个人都看见棋,但每个人看见的都难以归于一尊。从口中说出的那些话往往太远,总是太远。烂柯的一切都基于:变化的尺度。它塑造着,变化。变化在黑与白之间,万物的灰调子中。吊诡的是:石刻的棋盘上,仍卧着黑与白的子。一个棋局。也许他停止落子是出于更高的智慧。譬如棋界的大一统模型,我们最伟大的棋手也难以真正触碰,但只要棋局不动,就能找到一个刹那的绝对相同。也许他追求的是质:与其糊涂一生,莫若等待哪怕仅存于瞬间的真理。其实这是一种相当世俗的方式,如果未能等到,余下的将是失传与遗忘。
刹那间,有句话试图通过我的喉舌跑出来,而我的双唇像哑巴一样张开,仿佛除了一丝受惊的空气,还有什么正在他们之上挣扎。但它们终于没有发出声音,而我几乎就要想起来的东西,也像烂柯一样永远睡去。那睡去的神态似母子,是烂柯的神态,灰色的神态。不是死亡,而是久久的安详。
于是我说:失传同死亡一样并不存在。烂柯睡在永恒的安详中。紧贴着它变化的尺度。坐着,他是大山与人之影,躺下来,是大地的尘灰,温厚的身躯。
烂柯睡了,我——还有其他人,其他衢州人醒着,这就是出色。
(指导老师:卫中英)
微信公众号搜索: 北京小学学习资料 家长升学指南 家长升学训练营 关注公众号,获取最新资讯!

扫码添加“家长论坛”微信好友(微信号 16619908263)
获取叶圣陶杯初赛决赛真题、高清录播课/大赛获奖范文集锦+写作素材+写作技巧
咨询叶圣陶杯初赛 决赛政策请拨打电话 16619908263 (同微信号)
没有找到相关结果
0 个回复